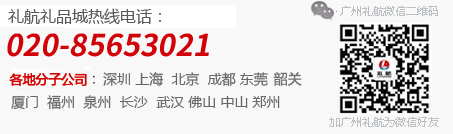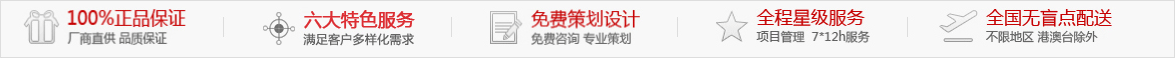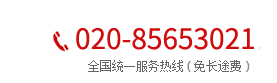我在国内的时候自我感觉也还算是会送礼的,虽然我不太喜欢送礼,也不喜欢收礼。这种礼尚往来俗气而麻烦。但遇到那该送该收的也算得当。我也自认为不看重礼物,凡收到的礼物大多转手送了人。我送出去的礼物除了很特别的,也大多忘记了。但是出国后,第一次因洋人邀请我们去过圣诞节,就因送礼的事让我不愉快了一阵子。
我先生从小在台湾长大,成绩优秀到想去哪上学就能去哪上学并且一路免学费还拿最高全额奖学金,他出国得早,更没有送礼的概念。在我出国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收到人家从另一个小岛发出的晚餐加平安夜邀请,我们都懒得出去买东西,先生就问我手里还有什么从国内带出来的礼物。
我手里从国内带出来的礼物几乎都是出国前朋友们送的,有的名贵一点,有的不贵但有特色,但说起哪一件来都是有其特殊价值的。结果就把这些都拿去了(国内送我礼物的朋友看到这里大概要气死了)。因为参加圣诞派对的人多,而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要送一份,主人特意告诉我们有多少个家庭多少个人,都是谁谁谁。我们也就买了包装纸把礼物全都包起来,写上卡片和名字。我当时是很有几分不情愿的。边做着这些事我边说,不知他们回赠过来的会是什么。先生说,全是一块钱的东西,老外送礼你还指望什么?我突然就停住了手,不高兴地问:“用一块钱的东西换我这么珍贵的东西?”
但是晚了,已经包好了。加拿大一些小城的店都关门早,再说出去也实在想不起该买什么东西。我对他这些洋人朋友的习惯还不了解,只知道那邀请我们的朋友喜欢中国的东西,一直把家布置得很有古典中国的特色。于是想一想,还是把东西送给他吧,东西么,就该送给最欣赏它的人才有价值。其他的朋友,了解更少,更不知道该送什么。算了,我告诉自己,不要太在乎,那不过都是一堆物质,只要记得这些送我礼物之人的心就好了。
我们于是在圣诞前一天早早地开车出去行驶一个多小时又乘了近一小时的渡轮到达那个小岛,进了朋友家。朋友原是在电话里告诉我们把礼物都放在他们的圣诞树下,大家会在晚餐后到圣诞树下寻找写着自己名字的礼物包。我们进门却没有立刻把礼物都放在圣诞树下,而是拎到楼上朋友为我们预备的房间里,想等到晚饭后亲自把礼物发在每一个人的手里,以示郑重。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本位主义的想法和举动。
洋人的晚餐是他们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早晨、中午都是一个三名治或汉堡。但洋人的晚餐虽隆重而在我们看来并不好吃。气氛挺好,点了蜡烛,有鲜花、水果和甜点心。晚餐后,大家离开餐桌都围坐到了圣诞树下,把自己的礼物找到带走了。我们也就从楼上把所有的礼物拿下来,放在楼梯口一个一个地发。大家拿到当场拆开来看,很高兴地说着谢谢,过来拥抱,离开。他们都住在当地,各自回家去了。我们远路而来,先生与他们又是多年要好的朋友,每次来都留下过夜。于是最后只剩下我们和主人家,开始坐在圣诞树下拆礼物。我们也就在这个时候把给他们夫妻俩的礼物放到圣诞树下。夫是夫,妻是妻,各有礼物,按他们要求的送,但送者却是我和先生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也就只有两份。我们没办法再拿出更多的礼物来,只这一次就把我所有朋友送我的礼物全部收刮干净了。
主人家太太把写着我名字的礼物全找出来堆到我面前,也把写着我先生名字的礼物全找出来堆到他面前。看上去很大一堆,其实都是这夫妻俩送的,左一个小包装,右一个大包装,都包得很漂亮。反观我们送的,从外部看那两个礼物显得很单薄小气的样子。那些其他已经收了我们的礼物离开的朋友,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礼物。其中一位在第二天一早复来敲门,让主人家转给我一本很厚的旧画册,是关于加拿大各地的介绍。
圣诞树下大堆大堆的礼物都是主人家的儿女们和远方的朋友寄过来给他们的,看上去很丰盛。他们需要有人与他们一起分享拆礼物的时光。也许就因为如此,他们才邀了我们来。大家坐在地上大拆特拆,发出夸张的惊叫声。其实就是一些睡裤、蜡烛等日常用品,还有他们认识的越南和泰国朋友寄给他们的檀香、调味料。东西不贵,加拿大不容易买到,在中国却不少见。我的礼物包里面是一些肥皂、围裙、毛巾、大小两只绒布猴子、一块钱一块的巧克力,东西果然都是从一元店买来的。北美所有一元店的货品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我先生的礼物包里,其中一包是两个木碗,还算特别,说是他的朋友亲手制作的,碗底刻着我先生的名字;他的另一包礼物是那位太太送的,里边也是一些香皂、毛巾。
他们送的东西是否有价值,要看你愿意怎么看。如果不是很惜物,扔一边去也没什么;如果惜物一点,不将人的感情迁怒于物,那么,这些东西反正都能用得上,用完了事。从这个角度看,倒是那两个看上去特别的木碗,对于常搬家常旅游的我们来说有点累赘,既不能用也不能转手送人,带来带去的颇多挪移,很麻烦。这都不算要紧,要紧的是我不想送而忍痛送出去的礼物,人家也同样不认识。其中一幅字墨是我的母校南大文学院认作镇院之宝的陈仲甫先生的论韵遗墨。百年校庆的时候,院系里复制了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返校的老系友,而在校生是没有的。这一部分复制的字墨放在全中国来看,也仅仅南大中文系的部分系友才有,仍算稀有物。字幅很长,我在国内时挂过它,贴着墙从天花板一直垂下来几乎到人的膝盖部位。字迹较小,字数很多,不仅一幅字而已,里边的内容即使给中国人看,也不是每一位都看得懂。它不是展示韵的,而是论韵的。专业性较强。那洋人朋友展开来一看,问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的英语连日常用语都勉强,没办法给他翻译;先生从没打开看过这幅字,打开看了也没看懂,理科人,即使他的英语超好也没办法翻译。那洋人朋友眼中现出失望神色,又问这是什么人专门写给我的原字迹吗?我说不是,复制品。他更失望了,卷起来放在一边。我当时很想收回来。
勉强在那朋友家里过了一晚,第二天回到家我就跟先生发脾气,说就用这些破烂就把我所有珍贵的纪念品全都骗去了,还被人家当成垃圾。其中一套黄玉首饰是我一位十多年不见的好友在我从北京登机前送我的,现在送了一个我们没什么来往的人。先生也没把这东西当成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向来对这类东西不识货,还会把真钻石当成玻璃或塑料,便说我那首饰肯定不值钱。我给他讲了送这礼物的是谁,你这样说是对我的朋友和我们友谊的亵渎。他被我弄得没法,又特意打电话给那圣诞节收到此礼物的人,说这礼物是国内一个很有钱的人送的,肯定很名贵,让她千万不要当成塑料。我一听,更来气,话被他一说咋这么市气?我那好友哪里很有钱?有钱人送这样的礼物反而不名贵,也没什么价值。后来那位被电话叮嘱过的朋友,发过几次邮件告诉我先生,她每天都戴着这套首饰,非常喜欢。但其后的几年里,我又见过她两次,都是在那邀请我们过圣诞节的朋友家里偶遇,那两次我并没有看见她戴那首饰。也许我当时没有留意。这样一来也才发现我并不是一直在乎这事。
在我到加拿大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邀请我们的洋人朋友,以后一直邀请我们,大小节日都邀请我们,他们的生日、我们的生日,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女来看望他们的日子,都会预先邀请我们去与他们一起聚会。还有后来的某年圣诞节,我们搬到东部又回到西部之后,再次应邀到那小岛去过圣诞节,我们随意多了,买点不算贵的中国茶叶,其他时候应邀前去,或带一件啤酒或买个水果派也就行了,有次带了一罐子腰果。他们回赠来的也都是更不成样子的东西,还有一件皱巴巴质量很差的中国文化衫,背部印着“不到长城非好汉”,也不知是他从哪弄来的。带回家后,连我先生都要随手扔进垃圾筒,反而这回我拦住他,留下了那抹布一样的文化衫,说穿着它干活还行,再不行还能当抹布用,比那留在东部与杂物一起堆到地下室的两个木碗要有用多了。这就是东西在我眼里的价值,与我在国内时候的价值观已经有些不同了。不是不再重视情谊,而是不再把情谊外化成麻烦的东西。不过这些老外送这些东西时都是郑重其事的,并期待着你收到后有个惊喜的样子,很多时候我也配合他们的期待。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中国人无论收到多贵重的礼物,都要表现得不太在意,还要客气一句:何必破费。
关于礼物,还有两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同样是这位洋人朋友,在先生将我娶到加拿大之后,这朋友恨不得抢在第一时间为我们举行派对。我跟先生说不要,我不是一个喜欢派对的人。那朋友还是找个时间把我们请去了他家,还接来了他们的两个小外孙女一起迎接我们,又请来一些他家的朋友,在晚餐时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相识相爱与结婚过程。在他们看来隆重在我们看来简单的晚餐过后,朋友离去,他们全家老小到一个房间里往外搬他们为我们准备的结婚礼物,大件小件的,搬出来也是一大堆。这事还是发生在那第一个圣诞节之前,我们很有些过意不去。打开看了看,全是红色的床上用品,很有中国特色。
他大概以为这样可以解我的思乡之情,却不知中国家庭早不再是这个风格了。而这些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东西,在中国很常见却少有人用,它们看上去土气土气的。我又刚从中国来,买中国的东西一定比他方便比他会买。不过这毕竟是人家的一片心意,我们珍惜的也是这片心意,所以回家后许久没舍得用这套床上用品,待到房子全收拾得差不多了,才真正好好地打开来铺在床上。结果发现那不是原本的一套东西,颜色都是红的,却很有差别。有新有旧,凑了起来。被套和枕套上面有图案,一碰,直往下掉金色的粉尘。睡前抖了一阵子金粉,觉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也不会再掉了,就用它们。睡觉时却感觉那被子上的图案很有摩擦力,不软不服帖,有点像塑料布一样哗啦哗啦的,早晨起来满床都是掉下来的金色粉屑,扫一阵子扫不完,于是将整个被套枕套翻过来抖,地上就密麻麻的落了一层。索性扔进洗衣机,洗出来一看,毛边都在外面了。便说,这人从哪买来的!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看看中国的东西质量有多差?那为什么他家还依然布置成中国风格?真是奇怪透了!
其实,许多洋人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朴素,他们买便宜的东西用,也以便宜的东西赠送人。而他们这些费力从哪买来的中国用品,即使质量如此之差,也还是比他们买当地有质保可退换的东西贵一点。他们住得离城市如此偏远,从小岛上大岛,从大岛再乘渡轮去温哥华一趟实在太不容易了。
反观加拿大一对中国夫妻,也是我先生的好朋友,他们送我们的结婚礼物与这对洋人夫妻送的礼物简直天差地别。在我被接出国之前,这对中国夫妻朋友就送我先生一张一千加币的支票,被我先生撕掉了,告诉他们,等她出来你们亲手给她吧。等我真正出了国,先生带我到另一个省去拜访他们,在他们家连住几天。他们真的把那一千加币换成现金放在一个大红包里给了我。又在洛基山上的路易斯湖(Lake Luis)渡假大酒店为我们包了一个总统套房,房价里甚至包括早、中、晚餐。这对夫妻朋友在国内时是大老板,出国后因语言有障碍,我先生帮助他们办了一些事。出于感谢吧,就借着我们的结婚送了这样的大礼。我们离开他们家时,将红包里只留下一张一百面额的加币,其余的全部放在房间里,待到离开那个省之后才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为我们准备在路易斯湖的总统套房,我们只住一晚就退房离开了,到附近自己花钱去住那有特色的小木楼。
另一件关于那位洋人朋友的事,是他们夫妻一直收不到我们的邀请,就有一次特意打电话问我们怎么不邀请他们?我们便邀请他们。我烧了几道中国菜,他们对我的红烧排骨赞不绝口,一直问我是怎么做的,工序怎样。但这一次我们又做了一件非常失败的事,就是把一瓶中国朋友送的1980年代的五粮液打开了招待他们,并告诉他们这是中国最好的酒。他们说句是吗,喝了一口,直叫Very strong(太烈了),要求换啤酒。这么上好的一瓶酒打开了,他们却只喝一口,以后再给谁喝呀?还是招待懂它的人吧。于是我们带在去旅行的路上,特意拜访我的一位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师兄,在师兄和他朋友那里再次打开这酒,并说了酒是为什么打开的。那师兄本是很喜欢喝酒也很懂酒的,我们在国内时随便喝点什么酒他都很高兴,但这一次他看了一眼那五粮液也很不热心的样子,好像有酒就行,凑合着喝吧。席间大家谈兴很浓,但没人称赞那酒一句。
对加拿大的认识,我就是几年里在这样一点一滴与洋人的交往里,积累了一些文化经历。而在国内的时候,凭着读书多一点,又是人文类专业,常做文化比较,常接触海外的中国朋友,我自以为很懂西方,在课堂上也经常现买现卖西方的文化信息。等到真正经历了西方生活,才发现此前的许多认识以及各种渠道听说来的消息并不完全也不可靠。我知道了至少在加拿大的洋人怎样送礼和待客。
洋人送礼的随意性最初让我很不习惯,常有受愚弄的感觉,久了发现这样的礼物收受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以后再选择礼物也不需要那么费脑筋,甚至一张卡片就可以了。而我也不记得以后我再买过什么礼物,送过什么人。
这位与我们一直联系密切的洋人朋友,无论我们离他多远,都会经常收到他们夫妻俩联名寄来的卡片。对卡片我也很不珍惜,青少年时代在国内赶卡片的时髦大家互相赠送,最后堆积起来几大纸箱子便再也不看一眼,卡片上也都是些千篇一律的赠言。胃口就是那时给败坏了,以后只要看到卡片就头疼。于是我以英语不好为借口,懒得回应。但老外就喜欢这个你没办法,无论你理不理睬他寄来的东西,他还照寄不误。有时实在过意不去,我也会回寄一张。有一年,我独自在东部的温莎生活,先生在西部,我就收到那洋人夫妻寄来的一盒中国食品,是糯米麻团,里边有豆沙馅的、芝麻馅的、五仁馅的、芋头馅的等等,外表也是颜色丰富,玫瑰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紫的等等。我又在想,他们住的那个小岛哪里会有这种东西?一看就是乘渡轮到大岛或者到大陆去了中国超市,而我住的温莎有许多中国超市,出门走几步就能买到中国的东西,比他方便多了。而且加拿大的邮费高,邮递速度慢,邮局还动不动就向政府罢工要求加添福利。
这朋友送礼的方式还跟过去一样,我打开那盒子却是感动的。口袋里装了几个(内有小包装)出去,送给一个自称喜欢中国食物的德国女孩一个,那16岁的白人小女孩小心地放在牙齿边小小的咬了一点点,还没有咬到馅,勉强在前齿嚼两下就吐出来,说她不喜欢,手指尖捏着那个小麻团好像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样子。我说不喜欢就扔掉吧。她啪的一下就扔在一个垃圾堆上,转身走了,仿佛被得罪。以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她喜欢中国食物。而以前她很希望与我一起吃午餐。
这德国女孩的态度和举动其实也小小地伤害了我一下,之后我让自己把她当成一个年幼尚不懂事的孩子了事。而对于从西部小岛寄来这盒礼物的洋人朋友,我第一次心怀感恩地专门出去选择一张感谢卡寄给他们。这个过程让我仿佛头一次清晰地感觉到,一张卡片没什么,但因他出门因他而花时间愿意站在卡片陈列架前面选择的举动以及回到家里认真写赠言和信封的举动,都是真诚有人情味的,与应付的态度明显两样。再以后,我收到他们寄来的卡片,头脑中都会出现一个他们为这张卡片出门站在某店一堆卡片陈列架前在选择的情景。其实多数时候,卡片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从各种画报上剪下有关中国的东西来,拼贴在一起,有长城有龙有灯笼等等。是的,全是甘愿的,而不想做的事情是不需要应付的。
习惯了加拿大的风俗,也就开始害怕回国。因为每次回国都为买什么礼物发愁。我的先生说他最早去大陆旅游,认识了一群大陆朋友,后来上网也认识了一群大陆网友。当他再去中国大陆拜访这些朋友,并不了解大陆的风俗,从加拿大的一元店买了几只印有加拿大国旗的瓷杯子,在迎接他的饭桌上,他把这些杯子每人一个送给朋友。聚会结束时,有人就把他送的杯子留在饭店的餐桌上,没带走。以后他再去哪也都没有买过礼物送人,有人要求他给带件文化衫,结果那文化衫在他的背包里背了几千万里,到达接收者那里却太瘦太小,没办法穿。他说干嘛呀,你不送他礼物,他不会说你坏;你送他礼物,他也不会说你好;而送他一件礼物,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件礼物,没事堆积东西实在没意义。
直到这时我也才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先生从认识我之初到我们谈恋爱到我们结婚,他都从来没有送过我任何礼物。甚至去见我的父母也都没有礼物,倒是我自己怕失礼而以他的名义为我的父母备了礼。那时,我对他的这些在国人看来的“失礼”也是感觉麻木的,与他一起经过许多生活的摩擦以后才回过味来,也曾有过受愚弄的感觉。但是感谢上帝,这感觉并没有延续很久。
我后来回了几次国,对过去一些十分要好的朋友也基本上没给他们带什么礼物。连去探访我的老导师都是空着手去的,这在以前从未有过。老导师见到我惊喜地拥抱,然后我们倾心交谈,离开时他送我走上大街,送出我很远,告别拥抱,我看见他眼里含泪,意思是你下次再回来不一定能看到我了。他根本没有留意我是否带礼物给他,以前在国内时我每次去探访他几乎用一半的薪水买给他的礼物,他也从没留意过。学生们孝敬他的好酒他全都拿到聚会上与我们一起享用了。
也许我们的生活圈子离世俗远了一点,校园内的文科人,关注点与别人不太一样。我知道我的一些亲戚是很挑剔这些事情的。与他们建立联系形成圈子的人也就滚成了一个雪球,在这个雪球的规矩里行事。否则有你好看的。不过无欲则刚。这也是中国人到了有事求人时才行规矩的原因。看上去很市侩,实则被生活被那种文化气氛生生绑架了去的。
上次我回国,我弟弟事先特意委托一个去东北出差的人给他带一个上好的人参来,他说我姐姐就要回来了,我让我姐姐把这人参带到加拿大去。我看了一眼装在一个精致的硬木盒子里扎着红绳的人参,笑笑说,让我带到加拿大去给谁?他说送给重要的人呀?我说加拿大没有重要的人,也没有不重要的人,更没有收这种礼的人。那些老外,送他们一个中国结,他们就很高兴。贵的东西给了他们,他们也不识货。弟弟遗憾地收起人参来,还想让我拿走,我说你留着送人吧,反而它在国内有用,弄不好人家还嫌它便宜呢。弟弟说就是。我看着他,看着这些身不由己的我的家人们,心里悄悄感叹,也很是歉意,我或许稍稍脱离这些人情世故的捆绑了,而他们还不能够。母亲已归土,父亲已退休,他们不需要更多地应付这世界,而两位弟弟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为他们的孩子操心一生,要继续在这世俗里同流合污。每到有这想法的时候,我都分外地渴望末日到来,让上帝快些对这世界好好地洗一洗牌。